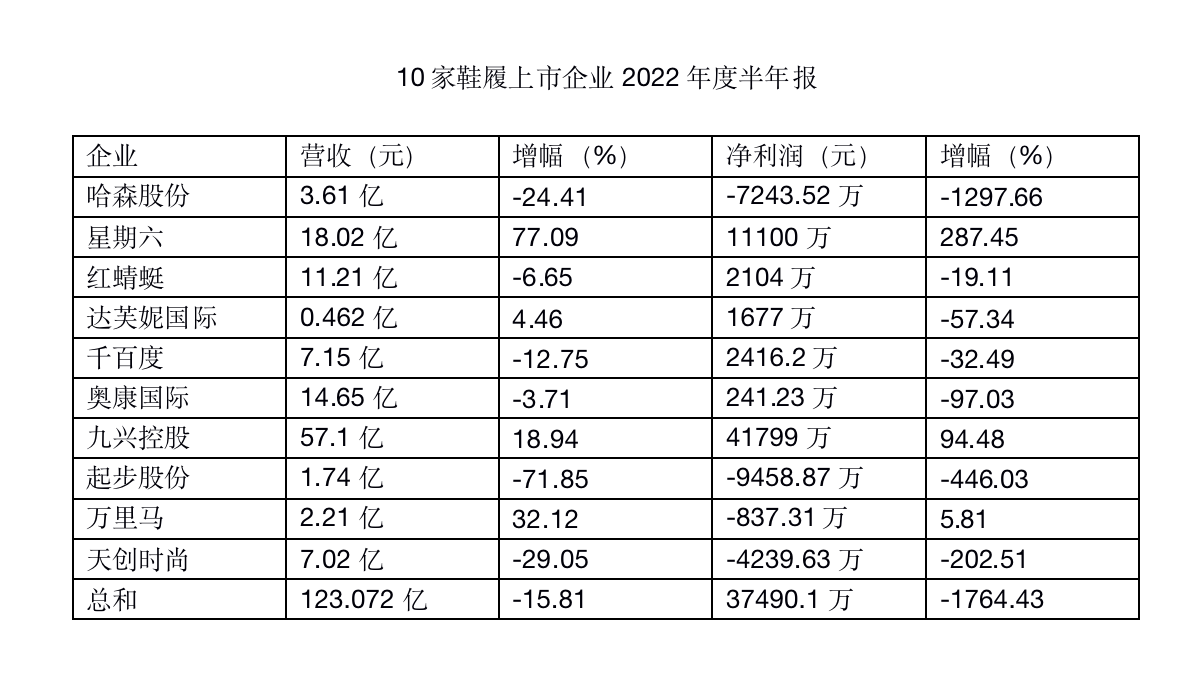冯家湾巷
学童们看见冯生走进学堂,都起立行礼,请冯生坐在教室席位上,然后各自回到自己的座位上,继续朗读着课文。冯生感到很奇怪,有如此自觉读书的学生,却看不见老师。他坐在位子上随手翻阅桌上的书文,原来是那位不知名的老师自己写的八股文。不但文章高华典雅,而且字写得细密端正。冯生问那些学童:“你们的老师到哪里去了?老师既然不在这里,你们为什么不顽皮的去和那些放牛娃一起玩耍,还端端正正地坐在课堂里朗诵课文呢?”其中一位年纪稍大的学童恭恭敬敬的回答说:“我们的老师是一个很正直的人,侍奉老母亲最孝顺,教育学生非常严格。学费收得很少,不够吃喝。他每天清早到学堂,对每个学生教好书后,就进山砍柴,挑到村镇,卖得钱后,这才踏着残阳归来,检查我们的功课。见学生中读书稍有疏忽,就喝令他下跪,有时用细荆条抽打。我们非常怕他,不敢放纵自己。冯生问:“你们老师姓什么?”学童回到:“姓颜”。又问:“叫什么名字?”学童们在课桌上写道:“髯樵”。另一个学生说:“老师因为长着浓须,以砍柴补贴家用,所以叫髯樵。冯生又问:”你们老师是秀才吗?”学童说:“不是,他没有钱去应考。”冯生又问:“顔老师住得远吗?”“他住的地方叫颜家坳,离这里有七里路远。”交谈刚结束,仆人已经骑马找来了,催冯生回去,说:知府有事找他。”冯生提起笔在黑板上写了“湘人冯子羽奉谒”几个字,然后向学童们笑笑挥手告辞回去了。
过了两天,冯生又专程去拜访,这时松树浓荫罩地,槐花开满庭院,颜髯樵还没有回来。学童们因为冯生上次来过,对他很熟悉,便热情地欢迎他,都捧着茶壶前来献茶。冯生代替顔老师上台授课,口若悬河,又如银瓶泻水,一点也不停顿。授完课后,他问学童们:“上次你们的顔老师回来后看到我的留字吗?看了以后说过什么?”学童们说:“只是笑了笑,他这个人本来就不太爱讲话的。”冯生说:“今天怎么还不回来?”学童们说:“听说近来柴价很贱,很难卖出去,所以很晚才到学堂里来。”冯生很觉得无聊,就随手在讲台上翻翻,看看髯樵最近写了什么新文章,果然发现了一、二篇新作,写的很出色,他就在髯樵的文章上大加评点,并对其中的小毛病做了修改,使全文成为无可挑剔的妙文。并且试着出了几道作文题留在讲台上。关照学童代自己向髯樵先生转达他仰慕之情,就很怅惘地离去了,对髯樵的思念也就更加深切了。第二天,他又去拜访颜髯樵。但是仍然没有遇上,讲堂上放着髯樵遵照冯生留下的文题写成的文章。冯生读后大加称赞。写了好多评语,并且留下文字预先与髯樵约定:某月某时请求一见,风雨无阻,请切勿错过。
到了约定相见的时间,冯生前去拜访,可还是没有见到一面,心里十分恼怒,责怪此人太不守信。学童们见冯生面带恼怒之色,就说:我们老师见了先生的批改文字,就趴在地上再三拜谢,每读一遍,就朝着先生离去的方向磕一次头。只是无奈他彻骨般地贫穷,不卖柴家里就揭不开锅。今天早上他特别关照我们说:“如果冯先生赴约前来,就请他稍等片刻,过了一个时辰就一定过来。”冯生坐着等了一会儿,一个学童朝外面看了一看,高兴地说:“我们的老师回来了。”冯生抬起头来,只见一位身材高大的汉子挑着一担柴大踏步地走了进来,年纪大约三十二、三岁。留着长髯,气度轩昂,看上去象一只雄鹰,头戴竹笠,脚穿芒鞋,真像朱买臣没有发迹时的样子。
花有清香月有阴,有才终遇求才人。若非相逢山界外,那得英名留到今。来时冯生尚睽违,不道从此衣锦归。若使人生皆到此,山中草木有光辉。